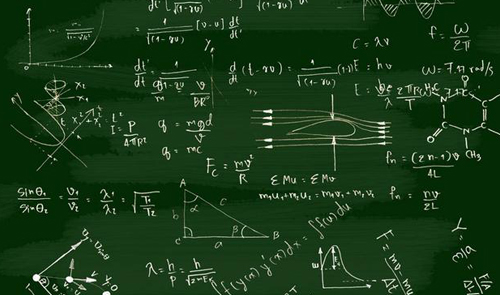如果你仔细聆听,就会听见日本特有的料理之音。这些声响并非来自一般的厨房,或是手忙脚乱的餐厅后场——至少和你习以为常的声音都不尽相同。你听到的,不是排队等着上菜的服务人员询问肋排何时烤好;不是炸炉内被炸至酥脆的结球马铃薯丝发出的嗞嗞响声;不是将酱汁以汤匙背面抹过盘面的声音;亦不是厨师用镊子夹起另一精选的香草,妥置在餐盘上的细微声响。
这些声音,是来自每晚花好几个钟头不断用绒布巾擦拭硬木纹理的摩擦声,只为了去除为顾客提供寿司时积累在扁柏吧台上的细微鱼油污渍;是指间掠过绿色咖啡生豆的沙沙声响,如一阵轻风拂林,好在烘焙前挑出有瑕疵的豆子;是挥动着手工扇子,调控备长炭火力的咻咻声响;抑或是以擦亮的木头捶打西红柿的细柔果肉所发出的低音;或是将细长的刀具划穿海鳗鱼身时演出的静谧节奏。
如此这般,全都是日本料理的音色。每道菜在为人品尝前,都以这类几不可闻的声音为开端,逐渐增强并富有力道。在迎来最完美无缺的那个瞬间时,在你始料未及的情况下,这些细微声响汇聚成一股强而有力的音爆席卷而来,而你唯一能做的便是合起双眼,任其激荡全身的感官。
如果说,这一切感觉起来都是那么珍贵,那是因为事实上正是如此。身在日本,特别是用餐的时候,最先体悟到的就是细节的重要性,不论是装点餐盘的红叶的角度、煎煮芦笋的师傅当天的心情,还是种植萝卜的农夫的家世。你和其他每一个人,包括经验老到的日本食客,或许大多会错失这类细节,但这并不重要;人们心里相信,料理人细腻的一举一动,能为食物带来近乎难以察觉的提升。若用明治时代的筷子来搅拌天妇罗面糊,就能让美味程度更上一层楼;而由头脑清楚、心情愉快的厨子煨煮的高汤,则会更加芳醇。
不过,并非每件事都有如此精细的工程。日本也有以肥美多汁的猪五花肉蘸上薄薄面包粉油炸,佐以大量浓稠的伍斯特酱和些微呛辣的芥末后端上桌的菜色。大锅煮的咖喱里则加入了苹果、洋葱和厚实的肉块炖上几小时甚至几天,锅里尽是一片深邃沉浊,好似一场突如其来的夏日风暴。此外还有由碳水化合物、高丽菜和猪油形成的巨大块御好烧,比起摆在日式榻榻米之上,这道菜摆在大麻瘾君子的咖啡 桌上还更显协调。
当然,不能不提的便是拉面,这也是所有日本食物中吃起来最不得安宁的。这种料理收录了各种拍打声、嘶嘶声、滴汤声跟啜饮声,就像一张原声带,颠覆着你对于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的认知。等等,那边那位拉面师傅该不会是随着嘻哈音乐的低音在切韭葱吧?哎唷,还真的是!
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如此让人充满惊奇。在这里,不管朝哪个方向转身,都能遇见让你惊心动魄的事物。
一切就从位于东京上方两万英尺高空的飞机开始。我还记得,第一次即将抵达成田机场的时候,飞机划破了云层,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突然在我下方展露原形,好似由数十亿个黄点所组成。 17 世纪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决定在此建立自己的城堡,当时这里还不过是 个小渔村。到了 19 世纪初,东京已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城市,有超过一百万人住在这座新兴的首都。长久以来,东京屡遭摇撼、粉碎、撕裂与祝融之灾,可如今仍旧屹立,无边无际,不断成长。
我在 2008 年秋季头一回造访了东京,那时没有立下任何计划,也没预订旅馆,对自己即将迎来的转变毫不知情。在这六千英里的飞行途中我完全无法入睡,于清晨时分步履蹒跚地踏上了地铁,并在东京湾迎来破晓之际抵达筑地市场外围。市场内就如同上演着一场海洋生物展:鱼腹饱满的鲑鱼、有着深色圆盘状外形的鲍鱼,以及难以计数的奇特甲壳类;而身躯散发光泽又新鲜的海鳗,看上去就像在泡沫塑料箱里打盹。我踉跄前行来到鲔鱼拍卖区,看见一名男子头戴挂有名牌的拍卖帽,在一片水泥地面上的好几百条银色鱼身之间来回穿梭。他双手迅速地比着各种手势,嘴里咕哝着只有精通鲔鱼的专家才听得 懂的行话。在拍卖结束后,我随着其中一条鱼来到买家的摊位。那里的一对父子挥舞着带锯、鲔鱼刀、切肉刀和片鱼刀,将硕大的鱼身按部位分切以供贩卖——结实的尾肉适合廉价居酒屋,如红宝石般深红的腰肉是饭店餐厅的首选,油花肥美如大理石纹路的大腹肉则会供应给高档的寿司名店。
到了早上八点,早已饥肠辘辘的我首先犒赏了自己一场寿司飨宴。十二种筑地的精华海鲜,诸如炙烧过的蓝鳍鲔鱼、富有嚼劲的北极贝、入口即化的北海道产厚实海胆,再搭配一杯杯冰凉的麒麟啤酒,我接连地将这十二贯美味冲下肚。之后在场外市场点了一碗热荞麦面,最后吞下如一座金色鸟巢般的成堆蔬菜天妇罗,划下圆满句点。时至正午,我站在邻近的高楼大厦前一个劲儿地傻笑,肚子虽然饱到有点不舒服,却又从来没有如此饥渴过。
要是你从没来过日本,就一定会和第一次拜访这里的我们做出相同的事:如卡通人物般对着所见之物不停地眨眼、揉眼睛;被涩谷及新宿汹涌的人潮淹没;由霓虹丛林跨入古老庙宇,再回归明日世界,见证过去与未来的奇妙冲突与共存。塑料制的食物样品、子弹列车,以及随处可见的贩卖机,无一不令人啧啧称奇,你甚至会连厕所都想拍照留念。在寄回家的电子邮件中,你势必会在字里行间塞满惊叹号。
面对这一切外在的刺激,你会感到毫无招架之力,却又同时感受到其曼妙之处。你可能会觉得无所适从,不晓得该在哪里转向,该向谁求救,或是该吃什么料理。
这最后一项,总是逼得我苦恼不已。要吃什么呢?自己可是横越了好几个时区来到这里,自然希望每一餐都能饱尝美食。要先从居酒屋,也就是日式的小酒馆开始,大啖生鱼片、各种烤鸡肉串跟炸豆腐,跟一杯杯冰凉的清酒一同下肚吗?还是选择熟悉的面条,如拉面、乌冬面、荞麦面等,任温热味美的面食华丽地滑过唇间?或者,也许你想一探未知的领域,品尝完全陌生的风味——一碗盐烤鳗鱼、一盘牵丝的纳豆,或是共有九道菜色的怀石盛宴。
在这方面你若是轻率地做出决断,就有些欠缺深思熟虑了。别搞错了一点:地球上最极致的飨宴,不在纽约,不在巴黎,也不在曼谷,而是在东京。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地展示了其多彩多姿、各有千秋的饮食文化,值得人们花一生去探索,但却没有一座城市比得上东京这座料理重镇在食物美味方面的深度与广度。
首先相异之处便是规模。相对于纽约三万多间的餐厅,东京则有将近三十万间(麻烦在这儿稍做停顿,体会一下这项数据的意义)。世上大多数地区的餐厅仅会坐落于街道两旁,但日本一栋十层楼建筑可能每层就有二至三间餐厅。这一栋栋的美食高塔,就好比巴比伦之塔一般直入云霄。
然而,东京之所以成为举世最叫人振奋的美食天堂,并非以量取胜,而是以质称霸。造就日本料理这般特殊性的因素繁多——对用料的执着、精细的技巧,以及数千年来的一丝不苟与精益求精。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术业有专攻。在西方世界,可以看到餐厅将味噌煮牛小排、白松露披萨跟柠檬腌鲈鱼同时放进菜单里,尽可能提供多样的菜色来吸引各种顾客。但在日本,成功的秘诀是专攻一种,然后把它做得好吃到不行,并且拼上自己的一辈子。有人毕生投入于烤牛肠或河豚刀工,抑或是从荞麦面团揉擀出富有嚼劲的面条——种种技巧都自成一门学问,且皆拥有无限的潜力。
所谓的“职人”(Shokunin),指的是深入并专一献身于各自技艺的匠人,而这种观念正是日本文化的核心。近年来日本最广为人知的职人便是小野二郎,作为纪录片《寿司之神》(Jiro Dreams of Sushi)的主角声名远播。不过,在日本饮食产业中,到处都能碰见像他这样专注不懈的人。沿着幽黑巷弄而行,顺狭窄楼梯而上,他们就隐身于紧闭的门扉之后,藏身于这个城市,乃至于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比方说,八十岁的天妇罗师傅,花了六十年光阴找出温度与手势带来的细微差别;身为第十二代传人的鳗鱼师匠,手持铁签好似针灸师运针,梳理着野生鳗鱼的肉质,将其美味引向新境界。而在父亲身旁成长的年轻人,年纪多大,在厨房修行的时日就有多长。这会儿随时都可能轮到他独当一面,而当这一刻来临时,他将会对自己该做的本分一清二楚。
日本雕塑家大馆俊雄曾在书中写道:“职人有义务尽其所能为社会大众谋福祉。这义务包含精神及物质两个层面。毕竟,职人的责任是满足需求,无论需求为何。”
东京这座城市中有一万名职人。你若是为了享受美食造访日本,就该是冲着这些人而来。
起初我并不明白这点。用餐的时候,我会找任何看上去有正统日本风格的店家,然后只吃拉面、乌冬面和天妇罗,并为此感到心满意足。直到后来,一位朋友Nohara Shinji带我去了家咖啡馆,情况才有所改变。他是名美食导游,看家本领就是把初访日本的游客变成死心塌地的日本迷。经营这家咖啡馆的大坊胜次先生花了四十年,把冲泡出如此暗沉混浊汁液的过程转化为宗教仪式般慎重的手续。每天早上,从好几磅的咖啡豆中一粒粒亲自筛选,每批再以小火手工烘烤三十分 钟。最后,就像在观看人生的倒带一般,看着手冲的每一滴精华缓缓落下——经过如此煞费苦心的工序,才泡出了全东京最醇厚、最昂贵,也最劳心费神的一杯咖啡。
当双脚跨出了大坊咖啡馆的那一刻,我对东京、日本,以及整个饮食世界已是彻底改观。我学会了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也有了持续回访的新理由——没错,除了来吃面、回转寿司和御好烧,更得空出时间去见一见这些深谙东京精髓的职人们。正是他们对于完美的低调追寻,丰富了这座城市。
银座是东京寿司文化的核心,因此也是日本寿司文化的中心,更是全世界最适合品尝海鲜的地方。只要沿着光彩夺目的街道走上一回,你很快就能明白个中道理——这里是日本最为富裕的地带之一。以此地为大本营的,除了奢华的百货公司,还有一系列的国际名牌精品店,各自拥有由著名设计师所打造的华美店面。要与全世界最昂贵的料理交相辉映,这里再合适不过。
我们今日所知的寿司,便孕育自银座街区。自 8 世纪起,日本料理人早已不断地赋予熟寿司各种变化。然而一直要到 19 世纪初,随着江户(东京的原名)作为日本新的首都逐渐成熟,才有了如今为人所熟悉的握寿司手法。那时,此区遍布着木制“屋台”,即街上贩卖食物的摊子,为城里人供应当日来自东京湾最新鲜的渔获。料理人握起一团温热的米饭捏制成形,再摆上一片新鲜鱼肉,一贯一贯直接送到饥肠辘辘的顾客面前。为了模仿往昔发酵的鱼那种酸得令人皱唇的风味,他们在饭里头加入醋;为了去除潜在的细菌或毒素,便在鱼肉上抹了些研磨成泥的山葵;为了调味,另外淋上了几滴酱油。现代寿司的原型——江户前寿司——自此问世。
今天,在这八条街的范围之内,荟萃了地球上最出色的寿司店。店内的料理台被擦得闪闪发亮,这些店家据说加起来总共摘下了十六颗米其林星。大师小野二郎的店便坐落于此,他的地位犹如日本寿司众神中的宙斯,由他提供的盛宴要价三百五十美元,出菜到结束不过二十分钟,外国访客与日本名流轮番成为座上客,来此一探究竟。斋藤孝司的店也同样在这里,他好比是年轻的绝地武士,有着全市最长的预约等候名单。当然,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店家。
在一栋不起眼的办公大楼三层,有一位寿司职人站在精致的双层山胡桃料理台后,以鲛皮擦菜板磨着薄荷绿的新鲜山葵根,准备服务第一批客人。有些人称他是东京寿司文化的灵魂人物。身为一名寿司师傅,此人算是年轻一辈,大约四十岁上下,体格健壮得像个橄榄球后卫。他双臂结实、理了个平头,用略带严肃的眼神取代大部分的言语。
我头一回见到泽田幸治是在 2011 年。当时我在吧台前找了个位子坐下,接着便逐步感受到自己对饮食世界的认知开始瓦解。把那次经验说成有如天启,恐怕还过于轻巧了点。在“泽田寿司”(さわ田)的那一餐对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一贯贯寿司就好比数首歌颂淀粉与海洋的诗词。即便严格来说并不完美,却明示着通往极致完美之路的确存在,亦是一道引人前往天堂的阶梯。而在这条路上,泽田幸治无疑正一步步朝着顶端攀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