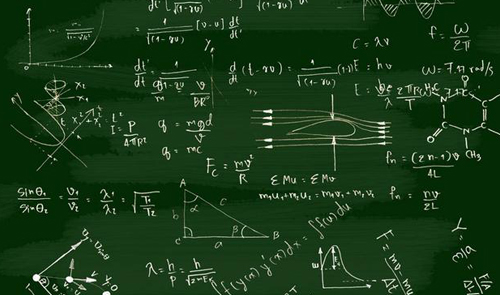我们用智能设备通话,借助导航设备穿越陌生的街区,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我的朋友与自己选择的配偶第一次步入婚姻殿堂后以失败告终,可现在却与计算机为他选择的伴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使我感到惊讶。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机器干预我的决定。我的手机上下载了一些天气预报的APP(应用软件),它们声称能够预知未来14天的天气,并精确到每个小时。一周刚刚开始的时候,软件里本周六的天气状况是一个太阳的符号,这令我感到很安心,因为计划好的游园会可以如期进行了。周日则显示的是阵雨的符号,于是,我早早地担心起约在当天的皮划艇项目。
如今,气象学家可以为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在法国近代早期,预测天气的人还被视为骗子,被绑到轮子上遭受轮刑之苦。俾斯麦也曾禁止引入国家气象服务,理由是普鲁士官员自己对天气的判断从不出错。如今,气象学家们凭借其对未来愈发精准的预测,影响着几十亿人的生活。
当下,对次日天气的预测准确率可达 70% 以上,而对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比我上大学时对次日天气的预测还要可靠得多。在这方面,计算机技术当然功不可没。 1979 年,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借助超级计算机克雷-1(Cray-1)——它是通过液态氟利昂冷却的——开启了天气预报的新纪元。当时,这台计算机每秒可以进行 1 亿次运算。如今,一块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计算速度比它还要快 30 倍。而目前用于气象预报的机器对德国上空的解析能力已可以精确到方圆 3 千米——这意味着每个村庄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天气预报。为此,这些计算机需要吞吐来自上万座气象站、成千上万的飞机与船只、几十颗卫星的数据流。
这个世界正在被扫描、采集、转译成机器可以读取的信息:我们以令人惊异的方式接近了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侯爵(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的幻想。 1814 年,这位法国天文学家提出了关于完美智慧生物的假说:“它足够广博,能够将一切数据都一并解析。”在这样的世界级妖精——人称拉普拉斯妖——的面前,任何事物都无处遁形。不过,拉普拉斯所指的并非全球性监控。他曾写道,他提出的这一智慧生物拥有的是预见未来的天赋。因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遵循着自然法则;如果能够足够细致地了解今天的世界状态,那么,明天的形势就可以被计算出来。关于拉普拉斯的这个想法不过是一次哲学性的思索。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大规模的数据处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在当时,拉普拉斯妖不过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构思出拉普拉斯妖是为了彰显自然法则的威力,从而推翻宝座上那位凭借自己的意志统治一切的神。有些人也许会追随他,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测的,其他人也许不会。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幻想已不再是幻想。在发明家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于德国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启用世界首台可编程计算机后,又过了短短 70 年,我们就已经能够处理海量的数据,想处理多少就处理多少,前提是得配置足够多的计算机。于是,当年提出的拉普拉斯妖就在计算机处理器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而且,处理器的性能每过一年半就会翻倍,仿佛没有什么能够再妨碍我们更加精细地预见未来。
如今,已具备了强大运算能力的互联网集团及情报机构希望能够细致入微地预测人类的行为。他们想要知道,怎样的广告能够抓住我们的心,下一次恐怖袭击的发生地会是哪里。医生希望通过基因信息预测疾病,甚至有神经科学家和部分哲学家认为,我们的大脑也是拉普拉斯妖分析处理的众多事件之一,他们幻想有一个数学模型能够代表我们体内发生的一切。你会诧异还有那么多人竟然害怕这类研究吗?这种不安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忧虑,人们担心被解析的世界会不再神奇、被解析的人类会不再自由。我们并不想被捉摸得一清二楚。
这种认为世界的一切运作是以少量的几个法则为基础,理论上能够被计算或预估的看法,被称为还原论(reductionism)。还原论仿佛皈依了现代自然科学,这类研究注重寻找尽可能简单而又无所不包的阐释。比如,我们能够飞到月球上,是因为宇宙空间中一切物体的运动都能根据一个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来;我们还能够凭借达尔文有关变异与自然选择的法则,解释所有生物的演化;而在借助量子物理学的各项方程式理解了原子的动力学特性以后,我们构建了一个满是计算机和激光的虚拟世界。所有这些成就都令我们对还原论的信赖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