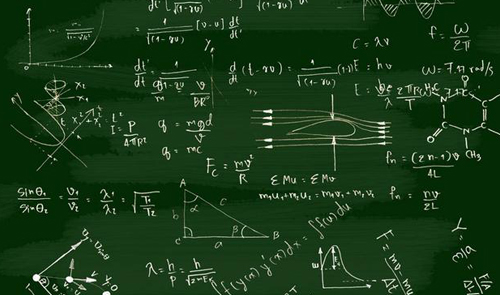本书的篇章将探究一种奇异的行为,某些诗人将他们的诗全部或部分地言说给他们既不认识也无法用眼睛看到的人,他们看不见的倾听者。乔治·赫伯特(1593—1633)对上帝说;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对未来的读者;约翰·阿什伯利(1927—2017)对一位过去的画家。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交谈对象的选择?有许多看得见的听众可选——爱人、恩主、孩子、朋友——为什么诗人感到非得与一位看不见的他者对话?与那样一位不存在的存在说话,带有何种伦理意味?要思考这一选择,我们须先来看抒情诗中更为常见的诉说对象类型。
在通常的形式中,抒情诗展现给我们一个单独的声音,它独自记下、分析、构划、改变自己的思绪。虽然实际并无另外的人在场,独处的诗人时常是在诉与他人,不在房间的他人。顿呼(apostrophe)——字面上表示转离自己的诗节(strophe)而呼唤另外的人——甚至被称为抒情诗的本质(虽然也有很多内心孤独思索的抒情诗并不诉与他人;那样的诗,阿诺德悖论地形容为“心灵与自身的对谈”)。一类可能在诗里缺席的言诉对象是虚构的说话者认识的一个人——一位情人,一位资助人,一位家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说话者可能说与朋友或情妇,多恩可能说与他的资助人,本·琼生说与他死去的孩子。这类与人的对话可被称为“平向”: 尽管诗人可能用一种正式的尊敬语气(在资助人的情形)或一种爱慕的温情口吻(在情人的情形),说话对象毕竟只是另一个人。但还有一类“纵向”的对话: 在这种情境中,说话者的呼唤朝向一个在构想中存在于其“之上”的、肉身无法企及之境的人或物。这个位于上方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基督教的或古典的)神,或一只夜莺,或一个希腊古瓮,可以位于天堂,在帕纳斯山上,或在一个融合了真理与美的柏拉图层面。在纵向的呼语中,说话者的语气超出了对世俗的恩人表示的尊敬或对所爱之人流露的仰慕,显示出一种适于对神言诉的谦卑。
许多诗人都提及过缺乏满意的人际交往时所体验到的孤独感。艾米莉·狄金森说:“这是我的信,给那/从未写信给我的世界。”表达丰富的诗人与冷淡的听众之间痛苦的不对等迫使她不断地写信给沉默的世界。因皈依罗马天主教而与家人和同学疏远后,霍普金斯问:“你在哪里,我永不会见的朋友?”他为这永不可见的朋友想象了两个地方。也许他只是在同代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在这个时代离散出我的视域”——但更可能是,鉴于霍普金斯不因循传统的性格和诗歌,这位朋友仍是那“将临时代的遥远承诺”
虽然霍普金斯看不见的朋友更可能活在未来——“将临时代”——而不是现在,诗人对他的口吻带着哀婉的此刻的亲密感,自信这位友人会喜欢自己的这个或那个特征。同时,霍普金斯知道,建立在一个推定的亲密关系上,在看似无法逾越的时间鸿沟之上,推崇宗教皈依这一“请求的微弱”。此刻的极度渴求将对亲密关系的欲望向前投射,想象了一个社群,能产生会在诗人的幸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伴。
在这些段落里,狄金森和霍普金斯将对一位相识的人的惯常亲密交谈转换为一种罕见的形式——对一位未知的人的亲密交谈。所有的抒情顿呼,无论平向还是纵向,都赋予我们各种语气,通过语气来比拟地展现我们在生活中所知的各类关系。抒情诗可以复制父母的温柔,情人的嫉妒,朋友的关怀,罪人的谦卑。这些诗歌揭示说话者身卷其中的社会关系,诗本身也常常内嵌了各种机构化的社会规范,如家庭、教会或宫廷之爱。可是,如果诗人不想表达这样的关系,而是要重新定义它们,应该怎么办呢?比如,渴望一个比教会所提供的更亲密的与神的联系;或试图塑造一种尚未被社会认可的男性之间的情爱关系;或寻求一种在当代艺术家中不合时宜却显现在过去的审美认同?当亲密关系的对象永远不会被人看见或知晓,却能被人唤出时,抒情诗内在而基本的创造亲密感的能力也许最为惊人。在这样的情形,未见的对方成为未见的倾听者,锚泊住诗人即将流入虚空的声音。
在此,我将考虑三位诗人的作品里创造出的与不可见者的亲密。乔治·赫伯特在传统的祷告中没有找到可以充分表达自己与神的关系的言词,便创造了一群新的语气和结构来与一位神交谈,祂有时似处于诗人之上的人类思想无法抵及的地方,但更经常是(平向地)栖居在诗人的房间里,在诗人的内心里,乃至超凡地在诗歌本身中。沃尔特·惠特曼在传统的社会交往或在他所知的诗歌中没有找到渴望的与男性的亲密关系,便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未来的读者同伴,有些像霍普金斯想象的朋友。在霍普金斯那里,这位朋友只出现了一次,而在惠特曼那里,理想的交谈者在前三版《草叶集》中一直被呼唤,创造并维持的亲密感也从当下的愿望愈加投射进未来的梦想。在《凸镜中的自画像》里,约翰·阿什伯利没有在自己的时代找到一位艺术家同行来分享他对部分曲变的形象的审美,便与十六世纪矫饰主义画家弗朗切斯科·帕米贾尼诺交谈,不把他当一位逝者而是一位正在倾听的活人。幻想着在寻常现状里不可得的新的人际关系,诗人暗怀了一个乌托邦,其中此般的亲近是已知的、可得的——这里罪人会找到从未预见的亲密语气来面对一位慈爱的救主,社会将允许男性间爱意的公开表达,艺术家——不再感到必须只符合一个具象或抽象的流派——会认识到所有艺术都把现实转化为美学上的抽象和变形。
一个诗人如何用语言和形式将看不见的对话者和他与对话者的关系变得真实,或者说,“亲密效果”如何跃然纸上?如我所说,这种亲密感的产生源于一种深层的孤独,迫使作者召唤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拥有的倾听者。不过,当下社会中的事物一定有参与创造诗句中理想听者的形象。诗人可能会为期望中的听者寻找文本证据(赫伯特这般在圣经中搜寻一位亲切而不疏离的上帝的迹象);又或,诗人可能会在纸上稳定并延长在现实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爱情(惠特曼那在未来的读者满足了在他的生活中总太短暂的情爱关系)。当目前生活中没有任何诗人渴望的亲密联系的迹象时,便可能在对现状的反抗中唤起浮想中的新对话者: 阿什伯利,一位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在创作《自画像》的时候无法在他的同代人中找到投缘的审美,从而(带着惊讶、欣慰和欢喜)发现了一位过去的画家,跟他自己一样展现出一种中和的创作手法——部分写实,部分抽象地扭曲。
虽然抒情诗里的说话者通常孤身一人,这种孤独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交往的环境,而只表示他目前展现的交往状况反映在孤独中,不是体现在与他人的“现场”互动,而是指涉在字词和智识中。抒情者必要的孤独使得偏向社会批评的评论家判断,抒情诗缺乏他们感兴趣的信息:阶级冲突,家庭和政治对性的干涉,社群的构造。照这个观点,一旦说话者独自在房间内,就不会发生任何有意思的互动,任何有社会价值的话题也无法被表述。
在创造了自我与他人的弹性空间的语言中,当然是诗人说话者自己的道德选择得以表述。每一次想象与神的相遇,赫伯特就选择了他所期盼的上帝;那个出现在眼前的神的品质,乃从赫伯特自己最好的伦理而推得。当诗人提出一个不妥的道德准则时(上帝应该为牧师找合适的“工作”,或灵魂的“尘与罪”要受应得的惩罚),赫伯特的上帝会想办法把错误的准则温和而坚决地置于一边。每一次构想期盼的同伴,惠特曼同样创造了一种伦理: 他的伦理不仅认可已有的民主原则(自由,平等,博爱),而且通过语气和隐喻将它们扩展到意料之外的领域——想象着选择爱人性别的自由,或是他与神的平等,或是他与“普通妓女”的友爱。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较少地谈论赫伯特和惠特曼的伦理维度,因为他们常常直言不讳自己的道德立场。阿什伯利通常不会被当作一个有道德考量的诗人,却在他所操控的变化多端的语调中,成功地显示了一整套伦理关系,从敌意到不屑,从爱慕到自否。在形式之外还有一个虚构领域,在那里,在阿什伯利创造与一位过去艺术家的一段关系时,我们在动人的描绘中看到具体化的嫉妒、爱、野心、恐惧甚至敌意这些特质,刺激着诗人同他的前辈之间的关系。在跨越好几个世纪的美学联系的诗里,阿什伯利的阐述与其衍生自的帕米贾尼诺的画一样孤独而醇厚:这两幅自画像中的任一幅,都在另一幅的呼应里获得新生。
对文学的伦理意义的考量通常基于个案史,来自希腊悲剧或复杂小说那样更社会性的文本。抒情诗则较少地靠叙述行动中的人物来传达伦理意义,而更靠可信的语气,诗人勾划和描摹他幻想的情感时所创造和使用的语气(可以是任何类型——恳切的,或凶悍的,或令人反感的)。在诗歌设计与另一个人的关系网时(或与一个想象中可与之交流的事物——一个瓮或一只夜莺),它所抛出的细丝(用惠特曼的隐喻)搭住隐逸在所有诗歌呼语里的“某处”(或某人)。召唤出的语气不仅刻画了说话者,还刻画了他与倾听者的关系,于纸上创造出他们之间联系的性质。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将亲密性比作心理分析时的谈话,但抒情诗人向外交谈的言词审慎不适用于分析对象或分析师的情境。诗人“写下的演说”必须服从(而对分析师说的话不会)结构和形式诗学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因为承袭自过去,与诗人意图重塑的伦理构想便可能出现矛盾或含混。只要每种二人关系都涉及(正义、尊敬、互惠、同情等)伦理维度,那么同样地,每次以诗歌表现两个人的关联也是。这种伦理维度在小说家或戏剧家那里,甚至在对他人交谈的诗人那里,都不言自明,却在看不见的倾听者的诗歌里更具挑战性。语言亲密模式的呈现——抒情诗最大的力量之一——可否被视为一种严肃道德活动的形式?
我研究诗人想象的与一个看不见的倾听者的奇特关系——无论是因为他是神圣的,还是因为他只存在于未来,还是因为他早已去世——如何可以在心理上可信,情感上动人,美学上有力。但这不仅是诗人对内心中的一场关系的中立描写: 他的目的是在读者的想象中建立一种更值得赞赏的伦理关系,一种比目前世上存在的更令人向往的伦理关系。这是这些诗人的乌托邦意志,欲望要召唤出一个尚未在生活中实现的——但设想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的形象。这种可能性跃然纸上,带着从生命中最亲密时刻所携来的温柔、奇迹和信心。与不见者的亲密是与希望的亲密。阅读这些诗歌时,我们在构想一种比我们迄今所知的(宗教的、性的或美学的)更好的亲密上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