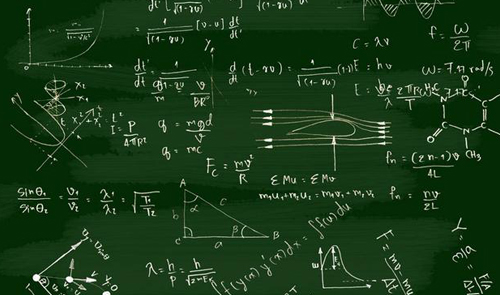加里曼丹是婆罗洲岛的一部分,属印尼领土,共划分为四个省份,总面积占该岛四分之三。这座巨岛中部群山环绕,森林蓊郁,北部则有两个马来西亚州:沙巴(Sabah)和沙捞越(Sarawak),以及小小的独立苏丹国文莱。
加里曼丹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十五人(爪哇则有一千零五十五人),但种族极为复杂。坤甸市长身上那种丝质礼服,是马来族穆斯林常穿的传统服装,他们的祖籍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早在欧洲人上岸前,已长期定居在加里曼丹沿海与河岸地区。加里曼丹内陆森林住着许多部落,现在统称为“达雅克族”,他们习惯在河边建造长屋集体居住,以划船或徒步方式进入森林开垦农地。 18 世纪时,华人曾在加里曼丹西部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近代又有来自爪哇、马都拉岛和印尼其他地区的移民陆续迁入当地,有些人是响应政府的越区移民计划,有些人是被加里曼丹南部及东部的油田与煤矿工作吸引而来,因此大约每五名加里曼丹居民当中就有一名非本地人。
我曾在偶然间看到一个取名为“印尼帮”的博客,后来通过邮件认识了版主梅兰妮(MelanieWood)。在雅加达短暂停留期间,我和她相约在当地雅痞常去的一家鸡尾酒吧见面。两人闲聊一阵之后,我提到了加里曼丹旅游计划,她立刻自告奋勇说:“我陪你去。”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那天她穿着剪裁合身的上衣、深蓝色短裙和一双式样典雅的绑带高跟鞋,我无法想象她坐在车顶吊着晕吐袋的巴士里会成什么样,于是赶紧向她说明我的旅游方式,她一点都不担心,没被我吓跑。
梅兰妮是个值得称赞的旅伴: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笑口常开、几乎对任何事都感兴趣。身材高大的她有一头闪亮的金发和一双勾魂的碧眼,我站在她旁边显得很不起眼,甚至不太像老外。她号召力极强,总能吸引一群孩子跟在她屁股后面,还会大方地为她摆照相姿势。
山口洋(Singkawang)是坐落在坤甸以北的滨海城市,从坤甸过去约需四小时车程,人口以华人占绝大多数,全市散发着浓厚的中国味,建筑大都为门面雅致的两层楼店铺,楼上阳台设有列柱廊和金属雕花遮棚,似乎仿自 1940 年左右的新加坡或槟城建筑,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落成的房子造型显得有些过时。抵达山口洋的头一晚,梅兰妮和我坐在露天咖啡座品茗,店家专卖一种看来有点像南非国宝茶其实是用达雅克族在野外采来的各种菊花所冲泡的茶饮。一群年轻人骑着伟士牌和兰美达1摩托车从我们身旁滑过去,拥有外形美观的复古摩托车是当地最新流行趋势,连崭新的本田摩托车都被改装成 20 世纪 50 年代的款式,骑士们也都戴着怀旧风头盔,丝毫不理会全国摩托车骑士皆须佩戴全罩式安全帽的规定。
我跟咖啡店的华侨老板贺曼托聊了起来,他提到山口洋的西方观光客不多,还打趣道:“我们这里最出名的只有人口贩卖!”我曾听说当地是邮购新娘生意的大本营,于是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山口洋确实有新娘中介业,但不贩卖人口。
新娘中介业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那时台湾企业大量采购西加里曼丹省的原木制成木材和板,到当地出差的台商发现山口洋居民当中有许多华侨女子,认为很适合介绍给经济状况较差的台湾老兵做伴,于是把这消息转告给台湾婚姻介绍所。后来这些介绍所协助男女双方鱼雁往返、交换相片,只要获得本人和家长同意,女方就嫁到台湾。贺曼托说,早期大多数新娘都是四十多岁——以印尼标准来看的老处女。“当然,有些男人会假装很有钱,女方过门以后往往大失所望,不过大多数人对媒合婚姻都很满意。”他指出现在未婚男女还是会通过婚姻中介牵红线,也促成了不少好姻缘,
“等待嫁娶的人可以通过 Skype 联络感情,而且机票又这么便宜,男方只要有空就亲自飞来探望女方,看看是否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当地某些新闻报道曾不约而同引用萨特里尼(Maya Satrini)说法,形容这些中介活动是“人口贩卖”。我从 Google 网站上搜索得知,萨特里尼是山口洋市立艾滋病委员会成员,于是就晃进城里,想看看能否在委员会办公室找她聊一聊,可惜没能见到她。她的同事们与贺曼托的看法一致,认为新娘中介帮台湾男人和当地女子牵红线,其实跟网络约会差不多。“一个是付费给约会网站,一个是付费给婚姻中介,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差别?”一位女士说。
主要差别在于婚姻中介必须确保女方家庭得到一笔聘金。纳聘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近来却被反对人口贩卖者挂上“贩卖”女子的污名。由于婚姻中介通常会和女方签订三到五年的合约,难免启人疑窦。而签约的好处是,万一婚姻触礁,女方可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返回家乡,情况类似印尼外劳依合约规定在马来西亚做完两年女佣之后重归故里。不过,婚姻中介合约明文规定,若女方婚后生子,抚养权归父亲。
“如果女方出身于贫穷人家,嫁给台湾夫婿大概是帮助父母最好的机会,子女孝敬父母在我们的传统里还是很重要的。”贺曼托说。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我从没想过印尼华侨中会有穷人。
印尼群岛最早期的人类活动纪录都是以中文写成,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大陆移民至印尼的商人,在当地经济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文化贡献也很卓著。生于云南的回族太监郑和将军,曾将伊斯兰教引进爪哇北部港口。不过,印尼人和中国移民的关系并不融洽。
事实上,最初移民印尼的华人,多数是在中国沿海家乡待不下去的商人,因为15世纪初的一位明朝皇帝禁止商业活动,以诏书颁布贸易禁令。于是这些商人就在爪哇北岸的一些港口安家落户,并学习爪哇语,娶当地女子为妻。 18 世纪中叶,爪哇至少有四座城市由华人统治。
华人也为爪哇带来了经商技巧,当地的王公贵族们推崇这些华商的生意头脑,常派他们担任港务长、海关员和收税员。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如法炮制,雇用华侨征收稻米税,以支应该公司对当地苏丹与亲王发动多次小型战争的经费。殖民政府不敢让人口众多的“本地人”致富,只容许少数华侨独占鸦片馆、当铺和赌场的经营权。
荷兰人也将大企业经营权——如在加里曼丹采金矿、在苏门答腊挖锡矿、在爪哇栽甘蔗、在苏门答腊种烟草和胡椒——出售给信誉卓著的华商。这些老板不雇用当地居民,而用船只从中国大陆运来数百名,有时多达数千名的华工,但这波新移民无须像过去的华侨商人一样融入当地社会。到了 20 世纪初,印尼华裔人口已超过五十万,其中半数住在爪哇以外地区,许多人的生活范围不出华人圈,而且只说家乡话,除了会改良祖传的家乡菜、祭拜和婚礼仪式之外,只知道埋头工作。
梅兰妮和我在山口洋意外发现了一家拥有老式“蛇窑”的陶瓷厂,蛇窑内部有条八十米长的隧道,末端是个蜂巢状的窑炉。工人说,这种设计起源自古代的广东省,不过该厂的蛇窑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我走进窑里,看见数百件陶器被排列得整整齐齐,而且浸泡过看不出成分的灰色釉药。窑内摆满一千件待烧作品之后,工人就用砖块封住窑门,然后升起窑火、添加木块。二十个小时过后,陶器上面那层如灰泥般的釉药,分别被烧制成明亮的橘色、褐色、绿色和浅蓝色,成为各式各样的陶壶、陶像和装饰陶龙。陶瓷厂的院子后方是座砖厂,一名瘦瘦高高、相貌清秀的中国北方青年,用独轮车推着满满一堆刚挖好的陶土,从工厂下面一个小池边现身。他稍稍揉了几下陶土,就把它们分成几大块,然后在两名女工面前拍打陶土。女工站在一张桌子前各自抓起一把陶土,压进一个长方形模子,然后用金属刀片将陶土上端削平,接下来把刚用模子“压印”而成的新砖块倒扣在桌上,每压出一块砖头可赚六十卢比,大约是美金四分钱。两位女工说,她们每天能压制三四百个砖块。我曾在南苏拉威西省看过这种制砖法,当地砖厂女工的双手因罹患麻风病变得又粗又短,老板则是一位身穿粉红运动套装的华裔女性。虽然印尼大部分地区的工厂都是华人当家,山口洋却有不少每日收入低于两美元的华裔女工。
我为此深感震惊,忽然意识到我也接受了印尼人对华侨商人的刻板印象。印尼人普遍认为华商精明能干、勤奋努力、极度排外、乐于慷慨解囊资助同胞,老想从印尼人的荷包里多榨些钱出来,所以愈来愈富有。
我在印尼东部认识的一位印尼商人曾说:“我替华人工作很多年以后,看到也学到了他们的优点,尤其是努力打拼。”但他认为华人生活空虚。“他们做每件事只为了钱、钱、钱,从早到晚只想到钱、钱、钱,过着吃饭、赚钱、睡觉、赚钱、翘辫子的生活,我不明白这种日子究竟有什么意思?”
印尼人必须仰赖勤奋、精明的华人为他们提供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因此难免对华人心生忌妒。 1965 年的反共排华运动,给印尼大众制造了报复的机会。 1965 年幸存的印尼华侨备受歧视,不被公家、军事或其他机构的欢迎,教育程度较高的华人在迫不得已之下,纷纷投入民间市场、店铺和小工厂。他们保持谦卑,力争上游,巩固在危难时期可资仰赖的亲族关系。这些关系和波波妈妈与松巴岛大家族之间的互惠关系相差无几,只是印尼华侨不会拿水牛当交换礼物,而是以商业合约及资本作互惠媒介。
当年苏哈托需要大批华人移民提供资本和商业网络,于是对华商释出垄断事业经营权,华侨买办也知恩图报,力挺苏哈托多项政治措施。印尼出口导向工业被注入大量资金,华商越来越富裕,尽管苏哈托惯用的伎俩是:一只手为华人提供好处,另一只手又把利益夺走。他加深了社会对华侨的歧视,导致华侨经营的学校、寺庙、报社被迫关闭,华人也被迫取印尼名字。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份澳大利亚政府出版物在一项引人注目的图表中显示,华侨掌控了印尼 80% 的经济,其中第十七条批注提到,该数字不包括国营事业或外商多国籍企业所占部分。另一项修订数据指出,华侨人口仅占印尼总人口 3.5% ,拥有的财富却比印尼人多八倍。
过去印尼统治者若想让民众宣泄政治不满,往往拿富裕的华侨当替罪羊,例如华侨社区曾在 1740 年首度遭到大规模攻击。苏哈托时代排华运动引起的大动乱,最终导致苏哈托下台,当年制定的多项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法律自此废除,印尼华侨相继成立双语学校,逐渐复原曾被捣毁的孔庙。一位华侨店家告诉我:“现在情况好多了,我的意思是,我再也不用成天操心店铺会不会被烧掉、能不能顺利度过今年了。”
梅兰妮和我的摄影老搭档恩妮一样,坐在我们租来的摩托车后座,跟着我在山口洋市区探险,只要发现有趣的事物,就戳我一下示意我停车。有一回,我们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看到一位华人老太太正在晾晒几排新做的面条。
我向她问好,但她不会说印尼话,于是我改用不太灵光的中文再试一遍,她立刻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们,这面条厂是她儿子阿辉开的,还邀请我们四处参观。
面条厂里的景象恍若第七层地狱,天花板上吊着一颗裸露的灯泡,一台略似中古时代刑具的大机器在灯下一边不停转动,一边发出噪音。身材瘦削、打着赤膊、汗流浃背的阿辉,把面粉、鸡蛋、清水倒入机器的一个大洞,它就啷、啷地旋转,叽嘎、叽嘎地震动,接着又发出喀、蹦、喀、蹦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我脑袋瓜里打鼓似的。那机器喷出一团臭臭的黑烟之后,乍然完全静止,原来是一颗螺丝钉松脱了。一名少年工人在面团里东探西探地捞出螺丝钉将它归位之后,又重新启动机器。最后,制面机吐出一大张面皮,工人先拉起面皮叠合压平,再把面皮卷在一根大木棍上,仿佛一大卷卷筒卫生纸。
工人在墙边一排凹槽架子挂满了卷好的面皮后,制面机就换上刀片开始切面条。一名长相俊秀、戴着一顶破旧红色牛仔帽的达雅克族男孩,站在这台机器怪兽的大嘴旁边,等它一吐出面条,就把面条披在几根油亮亮的木棍上,然后交给一组男孩挂到隔壁的干燥室里。那是个采光极佳、有许多吊扇的大房间,吊扇上布满蜘蛛网和煤灰,许多干面条像一排排窗帘似的被挂在吊扇下方,地板上摆着可加速干燥过程的生锈瓦斯炉,整个房间形同炼狱般热烘烘。
面条帘子再过去是装了临时门的厕所,离厕所不到一米处,有个盛满面条的热水盆在火炉上冒着蒸气。木盆里的面条煮软之后,就被包装起来配送给城里的街头小贩。
阿辉认为祖父创办的这份事业前景并不乐观,他儿子今年才六岁。“他长大以后不会想干这一行。”阿辉说,因此手下的工人全是达雅克族,“华人孩子会要求更高的工资,而且学会这门生意就不干了,然后自己办厂跟你竞争”。
我们告辞的时候,阿辉的母亲送了我一大袋面条。“能见到会讲中文的人真好,现在年轻人很难得开口讲中文的。”她说。
我回到菊花茶店后,跟贺曼托提起华裔后代不讲中文这档事。贺曼托说他父亲是中文老师,曾在他家屋顶藏了几本中文教科书, 1965 年排华事件结束后,他不敢违反苏哈托颁布的政策,始终没教自己儿子讲中文。“我是失落的一代,觉得自己的根被切断了。”贺曼托说。